我出生在陕北一个山高沟深的小山村,一条小河穿村而过,村民们世代沿小河两岸的山坡掏窑洞而居,村子里最红火的时候住着600多人,是远近闻名的大村,改革开放后,进城务工做生意上学的人多了,村子里住的人越来越少,最近这两年,偌大的一个村子只住了不到十个人,还都是年龄大的,以前的热闹场景再也见不到了。村子里人少了,牲畜也就少了,种地的都开着三轮摩托下地干活,野生动物越发的多了起来,石鸡、野鸡满山飞,野兔、野猪、狐狸钻沟上峁到处跑,每逢清明、中元、冬至,城里居住的人都拖家带口的回村上坟烧纸祭奠祖先,这几天也是村里最有烟火气的时候。
几年前,撤村并村后,周边的8个村子合在了一起,以前的村民委员会变成了村民小组,村里今年换届选举,新当选的村委会副主任和村民小组组长新官上任三把火,旧事重提,再一次把修建村民小组活动室的事提上了本届班子的工作日程。几天前,村子里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就村民小组活动室修建事宜进行协商,我作为书记员参加了会议,会上就村民活动室选址和新农村建设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协商,市镇两级有关部门也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基本达成了统一意见。当天晚上散会后回家,六岁的儿子在电梯里问我为啥要修新农村,我给孩子解释说为了能有个家啊,儿子又说我们不是有家么,我又解释到城里的这个是家,村里修建的是根,是让我们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个地方,是真正的家。儿子再说根是啥?我再解释,根就是一个人来的地方,爸爸出生在那个地方,是吃着那个地方的食物喝着那个地方的水长大的,对爸爸来说,爸爸的根在村里,爷爷奶奶的前半生都留在了那个地方,家里的祖辈们都埋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家,不论我们住在哪儿走到哪儿,根不会动,始终还在村子里。儿子似懂非懂的说,我的老奶奶就埋在那个地方,老奶奶就是我们的根,我笑着说对,你的根也在村子里,在黄土地里,我们所有人的根都在土里,土地给予了我们一切,吃的喝的用的都来源于土地,所以我们要感谢土地,你的名字里有个“ 植 ”字,希望你能把自己的根“植”在土里,不忘来路,勇往直前。
找到自己的根,滋养自己的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很难。秋末冬初,小区院子的美国梧桐宽大的叶子开始掉落,梧桐的叶柄有特殊性,落叶跨越的时间比较长,从秋末一直到第二年春天的新叶萌发,叶子掉落在路面上,环卫工人会每天进行清扫,清扫收集的树叶会被垃圾车收走送到垃圾集中填埋场进行填埋,“叶落归根”对梧桐树而言是奢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扎根开枝散叶,好不容易立在了一个地方,叶子找不到根,叶子回归不了滋养自己的土地,回家的路漫长而艰辛。梧桐尚且如此,何况乎吾辈,抬头三尺是远方,地下三尺是故乡。父母在年轻的时候从未想着有一天能离开村里,走出大山,费劲的在村子南头平整出一块宅基地,父亲更是雇了一辆推土车,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推出了一块可以修建一排窑洞的平地,母亲在宅基地旁修梯田、打水坝,汗水和心血都倾注在这块宅基地旁,宅基地和梯田上种植果树,父亲从县城农艺所淘换的新品种,丰水梨、香蕉梨、鸭梨、水蜜桃、蟠桃、黄元帅苹果、国光苹果、花牛苹果等都是村民不曾见过的稀罕物,母亲精心侍弄,不几年就挂果了,种的多自家吃不了,母亲就借上邻居的牛车逢集必赶,在集市上售卖,一斤不过五角,母亲还种了几架葡萄,那些年我们兄弟几个水果总是管够吃,不再整天惦记村里谁家的果树上的果子了。推出了宅基地,母亲又张罗着烧砖箍窑,村里不产沙子,就从十里之外的另一个村子拉沙子,自家没有牛车,就借用亲戚家的牛车,和泥制胚拖胚,都是自己亲自上手,雇的一个烧砖师傅,总计烧了三窑青砖,烧好的砖从砖窑拉出整齐的码放在宅基地上,箍窑的材料都准备齐了,就等着动工建设了,可这一等就是近三十年。
又过了几年,我和弟弟进城读书,母亲也跟着进城陪读,家里起先住的祖辈传下来的两孔窑洞也被遗弃了,再也没有住过人。两孔窑洞坐北面南,是陕北人说的人字窑,窑坐落在村子的正中间,两条小河夹院而流,窑洞的院子里种了一棵梨树、五棵枣树,一个磨盘立在梨树旁,院墙跟前有洋槐树数棵,粗壮而高大。院墙用石块垒砌而成,最上边夯土,奶奶在墙头上种了几株泽蒙花,院门是砖木结构,上覆青瓦。窑洞进深6米,主体是石头箍出来的,西边的窑洞里边土炕的里边还套着一个进深4米多的土窑洞,土炕的东边还套了一个存放衣物的小窑,一主两副,极为实用。夏天的时候,只要把最里边的土窑洞的门打开,睡觉的时候还要盖被子,冬暖夏凉都不足以形容祖辈的穴居智慧。我对这两孔窑洞的感情极深,始终无法割舍,至今偶尔还在梦里回到窑洞里,躺在土炕上,闻着土灶上柴草燃烧的味道,惬意的享受着岁月静好。我出生在西边的那孔窑洞里,在窑洞里度过了最快乐的童年时光,记忆里,母亲总是围绕着灶台和十几亩坡地转,脚踩着黄土,背靠着黄土,我会走路后也整日和黄土为伴,玩泥巴,跟母亲下地种种子,收秋捡拾谷穗土豆,对土地的感情之深,融到了血脉中,镌刻在骨子里。院子里用石头砌了一个露天的灶台,春夏秋季做饭就在院子里,春天的时候,我坐在灶台前,用力拉着风箱,不停地给灶台里填柴火,头顶的洋槐树正开着槐花,花香满园,蜜蜂飞舞,铁锅里咕嘟咕嘟的吃食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夏天的时候,日子悠长,母亲在地里劳作的时间也长,晚饭往往到了太阳下山后才开始做,我盯着灶头的红彤彤的火苗,用力的拉着风箱,期待着饱腹的那碗饭早点做熟,周围山头上的猫头鹰早早的开始了哀嚎模式,一声声的叫的我心里发憷。秋天的时候,我会推着磨盘一圈圈的转,新打下来的黑豆被沉重的磨盘一点点磨成豆浆,豆浆熬煮在灶头的大铁锅里,卤水点豆腐,豆香四溢,蘸着陈醋和切碎的红葱沫吃,口齿生香。
从小推磨盘,我长大后对磨盘倍感亲切,偶尔想起磨盘,就想起了我的团团转,仿佛有一根绳子拉着我不停的在打转转,绳子不断,牵挂割舍也就不断。离开村子近三十年,两孔窑洞也被闲置了三十年,村子里打坝拦洪,坝基越来越高,坝地面积逐年增加,现在已经延伸到和老屋院子一样平了,窑洞的松木门窗早就散架了,窑洞内壁的泥皮也全部脱落光了,靠东边的窑洞墙体垮落,窑洞已无法住人。里边的旧家具、黑瓷瓮等被跌落的泥皮覆盖,旧物件散发着土腥味、霉菌味,前两年我和弟弟回村的时候还钻进窑洞里把多年未动的东西翻腾了一遍,找到了好几张旧照片,还有一些唤起我们回忆的小物件。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进到老屋里了,日子缓慢的流淌,村里要修新农村的提议被村民采纳后,选址起先就定在了我家老屋的那个地方,计划着整体推倒加高后进行建设,我最先想到的是要把两孔窑洞中间窑腿位置的天地窑完整的取出来,这个天地窑镶嵌在两孔窑洞之间,细石面整体雕刻,高一尺有余,左右还雕刻了一副对联,留下了这个天地窑,也算是能留下点关于老屋的念想,把牵连不断的那个绳子留下来。
每次回村,我们弟兄几个都要去父母付出汗水拓而未建的宅基地走一遭,沿着曾经无数次走过的那条土路款步而上, 沿路有村里种植的一颗山楂树每年都挂果,无人采摘,欢喜了周边的鸟儿。周围母亲早年种植的果树早已死的死、荒的荒,特别是桃树全部都死了,葡萄每年地面部分的枝干被冬天的冷风吹干,第二年春天有冒出新枝条,循环往复。像被刀切了的土楞上酸枣树向阳而生,宅基地旁母亲早年为固土栽种的枣树长至一胳膊粗,沟地的旱柳长得分外茂盛,野兔子、野山鸡一蹿而过,高垒的青砖被风吹的散去了青色,显出了灰色,砖块上鸟粪随处可见。踩在土里,噗嗤噗嗤的声音,黄土更细了,坐下来,看着对面高高的那个山头,山头下是一块儿坡地,母亲当年带着我和弟弟在坡地上刨土豆,曾经挖出来一个砖块儿大小的土豆,我抱在怀里从村前沟走到家里,逢人就炫耀,仿佛从土里刨出了个大金疙瘩。
虽然土地里长不出金疙瘩,土里长不出白面馍,土里刨出的吃食仅仅能让我们不饿肚子,可我们从未对这片土地有一丁点的嫌弃,我们无比热爱脚下的这片土地, 想着有一天我们能叶落归根,回到这个地方,平静安详的葬于一丈黄土之下,子辈们能够记得他们从这里来,不论以后走的有多远,记得根在的地方。
奶奶去年走了,从黄土地里来,又回到了黄土地。她生前总是记挂这那两孔窑洞,记挂这她侍弄了一辈子的那十几亩土地,嘴里念叨着村里的人、窑洞、树、山路,村子的每一块儿土地是谁家的,那个沟道里那颗树是谁家的,那个坡上埋的谁家的先人,这些都记得清清楚楚。陕北人爱吃炖菜,甚至很长时间的烹饪手法就是炖和蒸,古人的鼎食就是炖煮,至今所有的陕北媳妇都能拿手的做上一顿烩菜,这与我们尊重食物、珍惜食物有很大的关系,炖煮的时候,食物的香气随着蒸汽上升,从土里来直达天庭,氤氲朦胧,仿佛早已远去的先人能和我们一同享受这食物的美好。几次给奶奶上坟烧纸,看着青烟扶摇直上,青烟在这一刻连接了地下、地面、天上的所有人,思绪远去飘散。
儿子一天天长大,能吃能耍,身体壮的像一头牛,完成了他的老奶奶曾经的愿望,成为家里的壮“ 劳力 ”,每次他一说起他的老奶奶,我就眼泪止不住的流,孩子毕竟还小,对生死的理解没有我们透彻,思考的少,忧愁就少,快乐自然就多,但愿他有一天能够明白父辈们对根的执念,完成父辈们对根的最后渴望。
路长且艰,愿你我都能叶落归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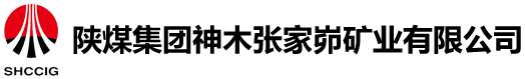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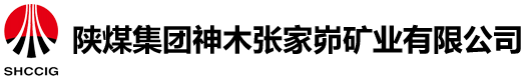



 发布日期:2023-02-10
发布日期:2023-02-10
 点击量:1178 作者:刘波 来源:
点击量:1178 作者:刘波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