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故乡是人们的精神家园。
每个人都有故乡,我总感觉出生在农村的游子更留恋故乡,更注重故乡情怀。其中的缘由我想也许是农村比较贫穷落后,农村的人们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都要离开家乡打工创业,去改变个人和家庭的命运。背井离乡久了,想念家人思念故乡的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强烈。不像城里人,生活在城市里,条件优越,养尊处优,到处都是水泥钢筋建筑,夜晚灯红酒绿,沉迷于现代文明的温柔之乡,自然也就淡漠了人世间最珍贵的亲情乡愁。激发不了城里人的故乡情怀。哪像我们农村,青山绿水,袅袅炊烟,鸟语花香,清泉山风。外出打工的农村人,虽然城里也有房,但总感觉缺一些情愫,感觉不到家的温馨。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总是思念故乡最浓的时刻,一有闲暇时间,总想回到故乡,回到生养我们的老家,看到故乡的一草一木,都觉得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激动。
但是,让人揪心的是,随着新农村建设,一些乡村已经慢慢失去了原本的朴实与宁静,现代文明也在慢慢蚕食乡村淳朴的民俗民风。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取舍。
我的故乡是秦岭以南丹江河畔的一个小山村。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故乡真的很贫穷也很落后。村子坐落在一个东西走向的山沟沟里,村子两头窄,中间比较宽,且地势平坦。有一条小河蜿蜒在村子的中间,把村子自然分成了南山北坡。来自泉山沟壑之中的这条小河,河水清澈甘甜,渴了、饿了的时候可以用手捧着或者用树叶掬着直接喝。河里有鱼,也有螃蟹,在那个粮食奇缺的年代,是这条小河滋润了我们的童年。那个贫穷落后的年代,每家每户不缺的就是孩子。村子里每个家庭都有好多孩子,少的两三个,多的有五六个,十个八个的也有。每家的条件也都差不多,家里大人们每天都要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辛勤耕耘挣工分,孩子们几乎就是放养,该上学的自己去,不上学的只能大的带小的。那时候,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学校,大一点的村子还有初中,虽然设施简陋,小学的课桌就是土台台,可离家近,离家最远的也超不过三五公里,学生全部都是走读生。村子的中学小学在一起,在村子的中间部位,村委会、卫生院、供销社都集中在这里,可以说是我们村子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的家就处在离学校大概一公里多靠坡跟的地方,依山建了三间土墙房,比较朝阳,只要是晴天,每天的阳光从早晒到日头落山。孩子们上学全靠学校老师管教,家长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管教孩子的学习,孩子家长见了老师会反复叮嘱,孩子在学校不听话,不好好学习就给我打。老师在那个年代是我们村里最受人尊敬、最值得信任的人。
也许是因为贫穷,在那个年代,可能有不听话、调皮打架的孩子,却绝对没有懒惰的孩子。六七岁以上的孩子,从小就能吃苦耐劳,每天除了按时上学,其余时间都会为家里做家务事。男孩主要是上山砍柴、打猪草、放牛、放羊,女孩主要在家做饭、喂猪喂鸡、照看弟弟妹妹,从来没有孩子叫苦叫累。
人们常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没妈的孩子像棵草,我有切身的感受。我妈去世的那年我不到四岁,家里姊妹五个,我姐最大也就十二岁。从此,我父亲既当爹又当妈,里里外外一个人,每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雨雪天气,都在生产队里劳动挣工分,可是每年粮食总是不够吃,每年春上父亲就得向左邻右舍亲戚借粮拉饥荒。为了度过饥荒活下去,我的哥哥姐姐没有进过学堂,早早地就参加生产队里劳动,为父亲分担家庭生活的重担,我才有机会进入学校上学,虽然很艰辛,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上小学初中都在村子里,虽然离家近,可是家里人遇到农忙季节顾不上按时做饭,我也有饿着肚子上学的时候,放学后忍着饥饿还得自觉地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左邻右舍家户的婶娘们看我经常饱一顿饿一餐的,平时没少接济我,那些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堂兄弟有时也会把家里的东西带给我吃,虽然那时我还小,可我一直心存感激。当时在农村每年的冬天是上山砍柴的最佳季节,这个季节要攒够来年烧火做饭和冬天取暖的柴,所以,每到冬季上山砍柴时,我总是带着村里的孩子们,帮着他们捆柴、背柴,安安全全把他们领回家。上山挖药材,放羊、放牛我也领着他们,可以说跑遍了方圆十几公里的山山水水。在这样的磨练中我慢慢地艰难长大,在家乡泉山环绕的沟沟岔岔山山水水留下了永远难以磨灭的足迹,也结下了永远难以割舍的深厚情义和生死情缘。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在那个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我能从小学上到高中毕业,最终没能考上大学虽然心有万般不甘,但我还是应该感到庆幸。是的,我没有资格没有权利选择我的出身我的家庭,可我庆幸有一个坚强勤劳无私的父亲,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的父亲是伟大的。是他教会了我吃苦耐劳,也养成了我的倔强与孤傲。我更庆幸我生养在一个青山绿水淳朴包容的故乡,是它滋养了我一生的真诚与善良。
高考,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从高考落地的那一刻开始,生长在农村的孩子就要做出人生的选择。我当时无依无靠,没有人帮我选择,父亲的选择就是让我拜师学艺做个木匠,可以跟着师傅走乡串村为人做嫁妆、打家具,混个吃饱饭。在县城三年寒窗苦读,十二分之差,就阻断了我翻越秦岭的人生梦,我岂能甘心?和父亲大吵一架,屁股挨了几木棍后,我怀揣着自己贩鸡蛋、收药材赚的五十元钱、背着书包内装着几本书一个被单,在一个天刚蒙蒙亮的清晨,没有人相送,一个人默默地走出群山环绕的村子,趟过十二次武关河,来到312国道边,搭乘一辆过路的大解放车,毅然决然,实则无奈地离开了生我养我十八载的故乡。先来到古城西安,后来在同学的推荐下,我去了韩城煤矿。这一去,就是三十五年,从此与煤矿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韩城娶妻生子,后又北上陕北。就这样,我的心时常在陕南陕北,陕北陕南纠结着、游荡着、挣扎着……好像都是自己的家、自己的故乡,又好像是彼此的远方。
现如今的故乡已变了模样,那些曾经贫穷落后的最初模样再也不见了。村里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已修成了柏油沥青观光专线,路两边的仿古路灯偶尔还能勾起我的乡村记忆。曾经低矮泥土房的桩基上已修起了砖混结构的楼房,少有的袅袅炊烟总会让我神情恍惚,取舍得失之间生发出淡淡的忧伤。已经改道到村子阴面坡跟的那条小河,不见了曾经欢快流淌的山泉,几乎干涸的河道里没有了翠绿的水芹菜,再也看不到畅游在清澈河水里机灵的小鱼和胖乎乎的小蝌蚪。田野里、山坡上栽种上了茶树,建成了茶园,很少有人再种庄稼,再也见不到春种秋收的繁忙景象。只是在每年的清明前后,有久居县城的城里人来村子里赏茶、采茶、品茶。原址上修建的新校舍,教学设施一应俱全,可是没有几个学生来上学。宽敞的大房子里,只有年迈的空巢老人,面貌一新的新农村缺少了人气人情。我也很少再回到故乡,即便是回来,也是匆匆的来,匆匆的去,好像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
大都市的繁华永远安放不下一个游子的心,新农村的新面貌新景象很难生发出浓郁的故乡情怀。是故乡抛弃了我们?还是我们忘记了故乡?经济的繁荣,物质的丰富,交通的便捷,通讯的发达,却让人常常感到空虚、无聊、无语、无助。心路的旅程竟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再也回不到记忆中的故乡,再也见不到梦中的亲人,剪不断,理还乱的悠悠乡愁,像雾、像雨,又像风。
故乡,渐行渐远的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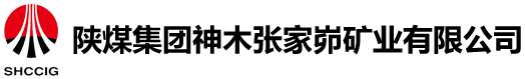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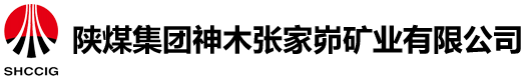



 发布日期:2022-11-29
发布日期:2022-11-29
 点击量:1503 作者:刘峰 来源:
点击量:1503 作者:刘峰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