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远的,便看见巧花孤寂的身影,她伫立在呼愣河大桥下,等待着心上人的到来。
她抬起头,看见钢筋混凝土桥墩攀岩而上的爬山虎,看见桥上来来往往的人群,特别是那些身穿裙裾的女子,沐浴着阳光,风轻柔地撩起她们的裙纱,像是有动人的故事要发生。可是,他还不来。
呼愣河没有了往日的湍急,河水缓缓流淌着,泛黄的河床高过河面却又紧贴着水流。河柳、菅草、臭蒿在河床上肆意生发,沙地上水鸭子、野鸡和雀子们的爪印清晰可辨,蚂蚱、蚂蚁和许多叫不出名的昆虫来回游荡。如果沿着悠长的河床寻觅,说不定能在繁密的河柳或蒿草林里发现一窝鸟蛋。可是,他还没来。
河边青绿色的芦苇长得将近一人高,密不透风。芦苇中间还有葱茏茂盛、英姿挺拔的河柳,芦苇和河柳遮住了明晃晃的水面。但蛙声还是飞溅出来,伴着间或传来的鸟鸣声。可是,他还不来。
呼愣河大桥上早已没有行人的踪迹,那些身穿裙裾的女子像被某种魔力召回。脚步声、嘈杂声和车轮声都隐匿,只听见风声、芦苇声、水流声……还有远处传来猫头鹰不祥的哀鸣声。巧花停下脚步,河水不知何时涨了起来,裹挟着浑浊泥沙的河水,渐渐向她逼近。可是,他还没来。
巧花皱着眉头,不时用手捋着掉下来的刘海。她也害怕、担忧起来,着急地在昏暗的河床上团团乱转。这时河水开始一寸寸、一尺尺涌上河床,好多芦苇和河柳已经被冲倒。她抬起头,看向桥墩旁唯一通上桥面的小路,还是没有人影,燃烧的夕阳隐没在山巅,只有大桥横亘在暮色苍茫的河面上。可是,他还没来。
巧花很害怕,呆呆地立在那里。
河水打湿了她的裤腿,她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河水像迎着风的火苗,肆意地漫延开来,也许很短的时间里,她的膝盖、腹部、胸部就会被无情的河水淹没。河水越涨越高,已经没过了她的双腿。可是,他还没来。
河水漫过她的腰间、脖颈,一下子,她就被卷入浑浊而湍急的水流中去了。此刻,四周静的怕人,只听见芦苇沙沙的声响,一切事物都笼罩在无边的暮色之中。一条鱼翻着白肚,从巧花的鼻子前面跳过。倏忽之间,天空挂上了稀疏的星子。可是,他依然没来。
月亮把皓洁的银光洒在河床上,岸边的河柳和芦苇在风中窃窃私语。面对死亡,大地上的所有事情蘸满了深情,它们开始聚集,像一场密谋已久的诀别,更像一场盛大的悼念。夜已深,河水把巧花的尸体托向远处。
巧花追求真爱、向往自由,也许她的魂魄向着澄澈的月色和自由的流水,她脱离了自己的躯壳,把自己的爱洒落在开阔的境地里,让天空、大地和更多的事物给她退让,这是一种难得的品质和境界。除了死亡,没有什么比取而代之更为重要了。人世间唯有真情可贵,但过分低估道德,以身试法获得情感是不可取的。
时光是一位睿智的检阅者。不管怎么说,巧花的等待还是铭刻在岁月的年轮上了,这种现实以及现实之外的隐喻,会永恒闪烁、跳跃着神性的光芒和启示。或许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愁绪和悲哀,都是另一个巧花,活生生地站立在生活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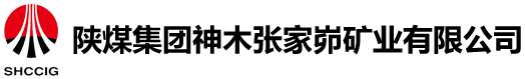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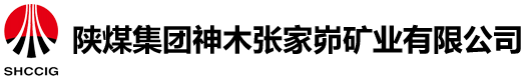



 发布日期:2022-11-29
发布日期:2022-11-29
 点击量:1485 作者:王永耀 来源:
点击量:1485 作者:王永耀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