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如门前考考乌素沟的流水,虽然水流细小污浊,还夹杂着砂石颗粒,可毕竟未曾有一刻断流过,蜿蜒流淌的日夜里,沿途汇入了太多的东西,依旧不改初衷,奔着窟野河而去,不曾倒流。苦难也罢,曲折也罢,喜乐也罢,欢愉也罢,人踩着时间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着。年关将近,去年走了的奶奶曾老说一句话“年好过,日难过”,她受尽了岁月的折磨,终有一天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跨越到了另一个轮回,好多经过她亲身实践和检验的富含强大哲理和韵味的话语至今仍在我的耳畔回响。
年好过,过好年!毕竟一年只过一回年,吃顿好的,穿件新衣,睡一觉年就过了,难的是日子要一天天过了,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前几天我居住的新区新开了一个综合性商场,号称“小万达”,以前给孩子买衣服不是去老城区就是去一百多公里外的“驼城”,现在省去了麻烦,避开年前购物的高峰,带着孩子去买过年的新衣服,儿子对穿衣这件事完全没有兴奋点,他的认知里,衣服穿着舒适就行了,新旧、样式、颜色完全无所谓,有的穿就行。新奇的事情太多,转移注意力的事情也太多,孩子一进商场,对选衣服挑衣服就表现出反感的情绪,心思早就游离在隔壁的游戏区,试鞋子,询问这个颜色是否喜欢?穿着是否舒适?可以自己轻松穿上去吗?回答的很干脆,喜欢,舒服。一旦确定好了,转眼就不见了人,孩子都有一种迷之自信,放在成人身上可以理解为赌徒心里,往抓娃娃机里投币仿佛给小兔子喂萝卜,不惜次数,一袋子币很快就见底了,最后剩一个币的时候,脸上由晴转阴,一个币是没法再进行最后一局的,我鼓动他去找其他的小朋友匀上一个,最后来上一局,腼腆又无助的他不为所动。给孩子买完衣服了,两个成年人默契的选择一人一双红袜子,新年新衣从脚开始仅止于脚。
我对过年穿新衣的记忆都在儿时,母亲嫁入我家的时候,家里条件很不好,生下我的时候,吃穿用度极为紧张,需要我的外公外婆不时接济,尿布都是穿破的秋衣秋裤拆剪下来拼接而成,顶替的都没有,我出生的时候恰逢数九寒冬,尿布洗了放在灶头烤干了再用,新衣服更是无从谈起,一块旧被套包裹起来就是一个冬天。我的奶奶是一个裁缝,准确的说是远近闻名的裁缝,裁缝手艺师承我的爷爷,爷爷和奶奶早年间远赴内蒙谋生,靠的就是裁缝和修理机械的手艺,后来从内蒙又搬回了村里,至此家里就多了一件值钱的家当——上海牌缝纫机。奶奶使用缝纫机是一把好手,手脚配合默契,一把剪刀使得出神入化,我小时候的很多衣服都是奶奶做的,母亲嫁入后,跟着奶奶也学习裁缝手艺,基本的样式和操作都会,至今那个缝纫机和锁边机的机头家里还保留着。奶奶生前按照自己的喜好给自己制作的寿衣,走的时候母亲给穿衣,我在旁边用手摸着奶奶的头发,整理着衣服,恍若奶奶还坐在床上用手一把把的抹着自己的衣服,寿衣合身还不显俗气,停灵的那几天,有一次打开棺材,我用手摸着寿衣,厚实的仿佛能把人世间的所有寒冷都隔绝掉。
小时候最怕冬天又期待冬天,夏天光屁股或者留档裤也过得很好,该上树上树,该下河下河,啥也不耽误。一到冬季,一条厚棉裤和厚棉袄过一冬,棉裤的外衬是万年不变的黑色或蓝色的确良步,耐脏还耐造,内里是棉花,棉花不是年年换,母亲每年把旧棉裤的棉花翻出来,重新梳洗,用手撕的蓬松一点,为的是冬天能让我穿着暖和点。棉裤上缝着松紧带,那种一指头宽的松紧带,方便穿脱,棉上衣缀扣子,大黑的扣子,为的也是我能方便自己扣上和揭开。棉衣里边是不穿秋衣的,穿上身子空落落的,如刚洗完澡一样,自己无法把控大小便的时候,棉裤开着档,小伙伴们在冰面上追逐打闹,滑冰溜冰一点也不觉得冷,再后来,棉裤闭档,冬天的日子就好过多了。母亲也会稍微的偷下懒,给我做衣服的时候总是要大一点,大一点第二年也能穿,不浪费布。过年的时候,母亲会做一身单衣,让我套在棉衣外边,颜色还是黑和灰,单独做个领子,穿起来也洋气的很,春天来了,脱棉衣穿单衣,一件衣服顶两季。
新年新衣配新鞋,虽然家里条件不好,我从小也没有赤脚走过路,给别人家做衣服剩下的边角料、旧的不能再旧的衣服是用来做衬底的,一层布一层浆糊,粘在石窑的面子上,晒干了就是做鞋底和鞋帮的主要材料,夏天做衬底浆糊不易冻住,干的还快,冬天的时候就往浆糊里加入沙蒿籽熬煮,黏性更大。鞋底和鞋帮的样子是奶奶传下来的,再后来赶集的时候会有新的鞋样卖,母亲也会买回来替换着用。鞋面用的条绒步,看起来时髦,摸起来手感丝滑,鞋面除了一整张外,母亲根据我的脚型变化,会在脚面位置左右各加入松紧带,穿的时候好穿不夹脚,脱的时候也好脱。几张衬底摞在一起,用手捻的麻线穿进穿出,针脚平整,间隔匀称,松紧有度,纳出的鞋底看着就是一个艺术品。大点的时候,我印象中母亲在集市中买回了胶皮的鞋底,看着像旧轮胎里拆出来的,鞋底还有切割的菱形花纹,有些更复杂,和现在买的成品鞋鞋底一样。我格外的费鞋,也别是小时候,一双布鞋没几天就磨的漏跟破头,条绒面的鞋子破一点,里边花色不一的衬布就显得格外明显,自己穿着不觉的有啥,特别是冬天耍上了冰,鞋往往是干着出去湿着回来,有时候实在是脚冻的受不了,就捡些树枝柴草笼上一堆火,烤干了继续玩。
我在三年级进入城里上小学,就没再穿过母亲做的衣服和鞋子了,每年新年的时候奶奶会带着我沿着城中心的钟楼附近买衣服,钟楼是这座小城的中心,南北东西四个楼洞像张着口的鬼怪神魔,把从洞口穿梭过往的人一世世都看尽,繁华的年头都数不清了,现在老街改造,我好多年都没去过了,不知繁华是否依旧。奶奶给我买衣服很少挑样子,更多的是要物美价廉,价廉属第一,好歹穿上了成品的衣服,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同学间流行穿西装,当了一辈子裁缝的奶奶着实没做过西装,带着我在裁缝铺扯布量体裁衣,做了一套我至今回想起还认为是最美最美的衣服。
母亲说起新衣服,总说起嫁过来的时候陪嫁的有的确良布,自己没舍得做衣服,二姑当时还没出嫁,在过年的时候用陪嫁的步给二姑做了一套衣服,二姑穿上别提多美了。奶奶和母亲对布有着很深的执念,父亲有一年在外开货车夜间在路上捡到两大匹布,也不知道是那个不着调的货车掉落的,当父亲把捡到的两大匹布拿回来的时候,奶奶都舍不得用,母亲倒是果断,扯了一匹做窗帘,用了好多年,直到后来搬家的时候,在床下翻出来,我还嘲笑奶奶惜布如命,放着东西不用。好多年,奶奶总是把面粉袋子留下来洗干净,拆开来一块一块缝在一起,当做套棉花褥子的套子,最近的十多年,面粉袋子都变成了编织袋,她才改掉这个习惯。
惜物如金,祖辈们流淌在血液里的生活智慧,我们选择性的继承,旧衣物不穿就捐出去,过年了,给孩子买上套新衣服,而给自己却是简单的有双新袜子穿就行了。日子过的长了,有些东西是自己始终坚持和关注的,有些东西,不在乎不执念,过得去就好了,谁的日子里还不讲究个性价比了,谁的日子里还没个奢侈一把的时候了。临近年关,过两天就要给奶奶上坟烧纸,母亲早早的就给买好了纸质的寿衣,念叨着上坟的时候给奶奶捎下去,新年了,在人世间苦了自己一辈子,在另一个世界穿的亮净暖和点。
过新年呀!穿新衣!企盼着年年穿新衣的孩子能快乐长大,在另一个世界的祖辈们将福泽后世,血脉永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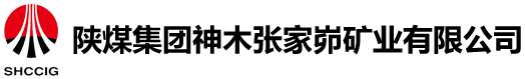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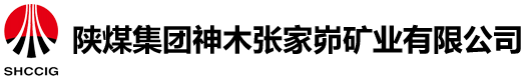



 发布日期:2023-01-13
发布日期:2023-01-13
 点击量:1400 作者:刘波 来源:
点击量:1400 作者:刘波 来源: